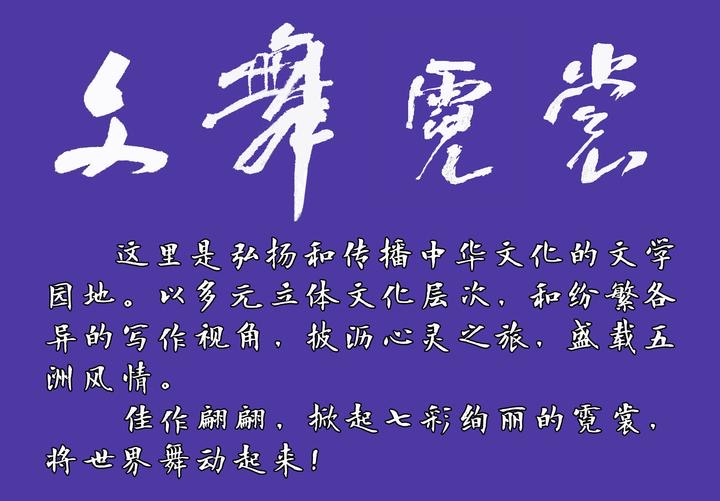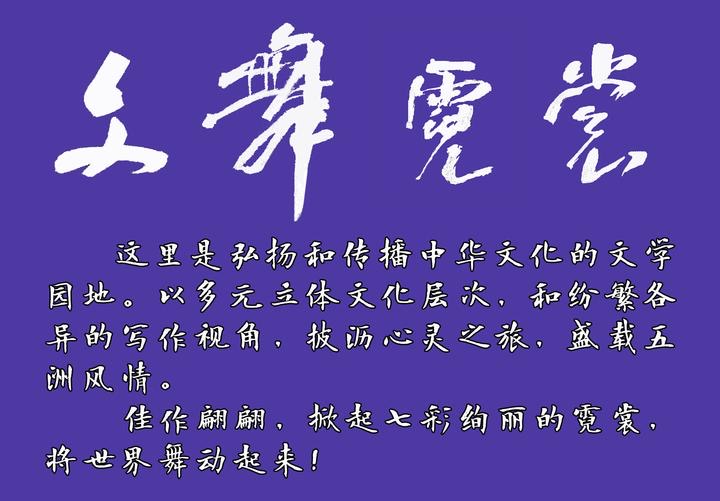■作者:李谦(中国)

【作者 李谦】1949年生,江西南昌人。南昌二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放本省进贤县捉牛岗公社插队落户,第二年任生产队长,第三年任大队副主任,1971年招工进721矿工作。从南昌市青山湖区劳动就业局退休,现随儿子居住上海,标准“老三届”。
有句话说:“人生是一系列选择的总和。” 那么如何来判断这个总和的成色呢?亏了?赚了?或是否值了?对叔叔而言似乎都不重要了,他只是无愧此生而已。
——题记

引子
不知咋的,想给叔叔立个传的念头随年纪的增大,越来越强烈。
一个画面,刀刻斧凿般印在了我的脑海。时间:1942年秋;情境:全国抗日形势胶着,滇缅前线战事正酣。一架由昆明转场的航空教练机在空中遇险,最后迫降在云南崇山峻岭之中,几个翻滚后,飞机解体爆炸,驾驶员不幸遇难,年轻的随机翻译从机中甩出,他发现自己居然活着,但遍体鳞伤,无法动弹,他在这荒郊野岭静静等待死神的来临。但命运眷顾了他,他在气力耗尽合上眼睛前,瞳孔中一个身材娇小、容貌姣好的姑娘来到了他的身旁,姑娘清澈得无以复加的美眸里充满惊慌与关切,接着,他便陷入知觉全无的昏迷……直至那一天醒来,眼中是简陋而整洁的茅草屋里几个人穿梭般的忙碌,还有后堂漂出的诱人的鸡汤香味!于是,草屋里传来姑娘惊喜地欢叫:“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旁边一对显然是姑娘父母的中年夫妇,如释重负地望着这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身着航空服的年轻人,额手向天;年轻人艰难欠起身:“谢谢你们救了我!”声音虚弱,充满真诚,感激之情无以复加。
那个被姑娘从死神手中夺回的年轻人,就是我的叔叔 ——李宗葵!不得不说,这个叔叔醒来后草屋里的庆生场景,是我后来脑补出来的,我坚信这古往今来的感恩剧情,一定都跳不出这令人唏嘘的桥段,更相信从那一刻起,叔叔生命中最美的珍藏便植根于心。
再以后,叔叔因伤势严重,不得不在姑娘家留下来,姑娘一家尽其所有,对叔叔照顾得无微不至,那姑娘更是把整个心都贴在叔叔身上。一来二去,叔叔不免与这位心地善良的美丽姑娘日久生情,直至康复,才子佳人的故事终因天作之合而水到渠成,他们婚后生有一女。再后来,叔叔常常于屋外凝望着空中隆隆飞过的战机,像只自艾折翼落单的大雁仰望高天的雁群。这一切都看在姑娘眼里,姑娘娇小的身躯竟藏着一颗深明大义的心脏,她知晓她们孩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到了必须归队的时候,因为丈夫平日里常对她说:这个国家还在遭难,我们得保卫它!
分别的那天终于来了!那还是一个秋天,两年后的一个秋天。不知那次秋风萧瑟中难舍难分的相送,他们有没有约定,有没有海誓山盟,但那个时代的气息是壮烈而真实的,国家兴亡面前生死未卜不值一提!叔叔走了,风萧萧兮易水寒,此一去,果真是永别!
叔叔的选择
洞悉叔叔的这段故事,是我有心为叔叔写点什么而获得的。这场乱世中的凄美浪漫让我动容。它加快了我作文的步伐。我列好了十几个题纲,向远在河南的堂兄妹——叔叔的子女以及武汉的姑姑们求证,还同他们视频;仔细阅读叔叔自己写的简历,力图从那可能因避讳而闪烁其词、一笔带过的文字中辨别其本真;贪婪地翻阅查找有关资料,然后辩识,推敲,演绎;我从未有过地为一篇文章成篇而脑汁绞尽,甚至夜不能寐。
由于时间久远,或是叔叔自己的过往不太愿意向人言说,向河南堂兄妹们的问询不很理想,好在堂妹李俊的丈夫张志鸿提供了不少内情。张志鸿这人善解人意,博学多才,叔叔生前喜欢同这个二女婿谈他的一些心事,算是“诗向会人吟”吧。然而在我的近乎学究味的严谨面前,张志鸿对有些事也不能完全肯定,我后悔没有在叔叔生前与他来一场细致到微末的畅谈,这既是为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也是力图从岁月的长河中打捞拼接出一个本该顶天立地,命途却总是与多舛与坎坷相伴的叔叔,还原本该属于他的光荣。但叔叔人已不在,往事难追,好歹就这样了,正如历史有时候也有缺憾一样。
叔叔是1939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的,与我父亲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在重庆,都是为躲避战乱而内迁来的。但叔叔没有安心读书,而是在1941年大二没读完就参军入伍,抗日保国,这使我一度觉得只知偏安读书的父亲与他相形见绌。叔叔那次报名入伍,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以致我在向武汉的姑姑们电话求证时,她们都云里雾里:“啥?还有这种事啊?找不到(武汉话:不知道之意)!足见叔叔投笔从戎之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写到这里,我恍惚在历史的光影中,看到当年的大重庆防空警报响起,不得不随众人一同躲进防空洞的叔叔,他在心头火起,怒发冲冠!

叔叔入伍后,很快编入了战事正酣的远征军系列。
资料显示,远征军成立于1941年下半年 ,为的是确保中国大后方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安全;在境外拖住日本主力,给国内减小压力;迎合当时同盟国的要求,开辟反法西斯的东南亚战场并使之成为主要作战地区。远征军曾两次进入缅甸展开对日作战,分别是10万和40万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远征军理当名垂青史!
心太软,每每阅读到远征军前线将士们在缅甸战场之惨烈,常会不忍卒读。
认真辩识叔叔的从军及抗战脉络后,知晓叔叔倒是没有经历例如过缅甸野人山和枪林弹雨之类的残酷,因为加入远征军系列的叔叔外语专长很快得到重视和极好的发挥。那时,盟军支援中国抗战的各类新式武器及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来国内,叔叔和他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把它的使用说明译成中文,前线战士很快就掌握了其性能,使这些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个事例:1942年4月,在缅英军撤往印度的过程中,英缅第1师这支七千多人的部队被日军包围,在中、美,英,印,缅五方商量救援无果的情况下,幸而得到手握新式武器而士气大振的中国远征军的相救,远征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数倍于自己的日军,最后使全部英军成功脱险。这场被称为“仁安羌大捷”的以少胜多的救援,创造了二战史上的奇迹,声震世界,以致几十年后,英国首相来华时,特地为这件事向中国表示感谢!张志鸿说:“我爸他们真的是功不可没!”
叔叔出色的笔译口译能力,使他成为当时战场的稀缺人才。那时,为取得对日军作战的制空权尤为紧迫,在盟军的帮助下,中国柔弱的空军得到了重建,中美联合的空中优势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我看过叔叔在八十年代向职称评定部门递交的简历底稿,出现过“昆明空军第五总站、呈贡空军第四十九站、印度(当时印巴尚未分治)喀拉奇基地指挥室、拉贺尔中国空军航校”等名称,叔叔先后都在其中当过翻译,这包括叔叔从云南大山归队后的经历。我查阅资料想知道昆明空军第五总站是咋回事,原来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也驻其中,而第十四航空队正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之一,叔叔在总站里如何干的,不知他为什么没有说到过;而那个“喀拉奇基地指挥部”,他告诉过张志鸿:是东印度英軍总指挥部,是中,美,英商谈軍事的地方。叔叔能被这个机构认可并调用,足见其优秀!
所以,叔叔应该是文职人员,曾思忖过他除去那次云南大山大难不死的差点为国捐躯,至少要比冒着枪林弹雨更安全一些,但我相信,他的作用绝对比自己扛枪上战场要大多了。
我曾有过疑惑,一个大二还没读完的外语系学生,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再一想便释然了,一个人报国之心满满,杀敌之心怒张,加上他的专研与勤奋,那种潜能是无法估量的。
叔叔的这次选择,改写了他后半生,全因为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了他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我将在以下“我与叔叔的几次遇见”形式中逐条深入交代。

我与叔叔的几次遇见
我与叔叔相处大约也就三、四次,时间总计大约不到一个月,这指的是有记忆以后,之前就难说了,因为父母告诉过我,我出生时,叔叔曾预言:“此子天庭饱满,来日必成大器。” 说明我小时候是与叔叔住同一屋檐下的。尽管我到老都与“大器”无缘,但叔叔这祝福式的预言还是让我对他心怀好感。
我出生在汉口汉正街,那里有条李家私巷,爷爷排行老九,被巷子里的小辈们称为九爷爷。我两三岁随父母来南昌后,叔叔一家因支内也去了河南郑州,从此天各一方。中途有几次随父亲回武汉探亲过,依稀记得见过一次也在武汉探家的叔叔,那次爷爷带我去巷子里拜望与之交好的三伯爷,现在回想起来,整条巷子式微中仍有点大家余韵。那次拜访,叔叔好像也在的。
成人后第一次遇见叔叔,大约是“文革”之前,那也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南昌的家,看得出叔叔那次心情不错,因为他的右派帽子不久前摘了,已经回到了原单位上班,而此前他一直是同一群右派在市东郊进行毫无自由的“劳动”的。所以他那次的来访多少有点向大哥报安的意味。那时我还在上初中,不太懂人情世故,对大人们的交谈几乎没有兴趣,更遑论参与或辩识。只是知道叔叔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且解放前还有很多历史问题,被划为右派后被整得很惨,而现在终于摘了右派帽子了,仅此而已。等我经历了此后的十年,方知“摘帽右派”这个名并没有其物理性实质,因为我看到很多摘帽右派依然被归于“横.扫”之列,“摘帽”?革命群众才不会理睬这一套呢!所以他们的命运依旧悲惨。今天看来,那时的叔叔还是不乏天真,有点像鲁迅笔下捐了门槛的祥林嫂。
叔叔那次还同父亲一起上了庐山,在那里合影留念。哥俩是在庐山分的手,父亲后来总会向我们说起叔叔分别时对他说的话:“大哥,我们兄弟这次分别,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再见面了!”说完,总是掩面而泣,看来木讷的人内心不一定没有情愫。

第二次见叔叔,是1988年春天,那是叔叔第二次来南昌看他的大哥,能清楚地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记住了叔叔脸上那抑制不住的喜悦,他的右派问题在八十年代初便已彻底改正,正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改开后的经济大潮让叔叔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被很多部门与企业慕名聘请去翻译资料,参与企业同外商的洽谈,任过多个业余大学的英语老师,他还是很多退休者协会和大型集团专家组成员。他为本省外宣而翻译的《洛阳牡丹》,更是被很多国外知名刊物转载,据传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宣部门采用。
那次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也参加了他与父亲的畅谈。叔叔谈兴很高,他这才说到了因为他的那段参加抗战的经历,解放后因不被人理解,反倒成了“历史问题”,甚至成为罪证,所以每次运动都被提溜出来,被审整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比如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还是因为那点“历史问题”,与口舌无关,尽管那年月他已经懂得该如何自保了。叔叔说,那些年,他一听到“运动”二字,就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以致人都会发抖。“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他长舒一口气道。
叔叔为人热情,很重亲情,这性格比我那内向的父亲更容易让人有亲近感。他叫我名称“谦儿”的声音很好听,那语音里带着拐弯味儿的亲切,至今让我言犹在耳。
“谦儿,我的右派问题当年给你们造成影响了吧?对不起哈!”那次,叔叔问我的声音很小心,很柔软,他面有歉疚。我怔了怔,忙说“没有没有!”心里却在打鼓:我从上学、下放、工作,以致入党,填表从来没有出现过叔叔,也就谈不上影响,我深知如实填了,只会为自己减分。但叔叔不这么想而已,他认为对组织应该忠诚老实,老实就应该会如实说,如实说了就会受影响。叔叔曾为我担心,我却从没把这为我担心过的人当回事,这愧疚,那一刻,生根了!
最后一次见到叔叔,是1989年夏,是在河南郑州他的家里。那时我在下海经商,我要去河南禹州取几种餐具,禹州自古出钧瓷,挺有名的,我想把它推介给我的香港客户。因为我那二儿子正值暑假,所以那次我带上了他,我们是一路辗转先到的禹州,在瓷厂取样返回时到叔叔家的,拜访叔叔在我的计划之列。
叔叔见到我非常高兴,在他那30几平的房子里接待了我,因堂兄李诚还在外地,他还把我的几个堂妹召唤来了。他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菜,叔侄俩喝了点酒,他的谈兴很高,饭后仍拉着我聊天,他告诉了我很多自己的事情,他再次向我解释了他的“历史问题”,他说到了打成右派后,从1958年到1961年,与很多同类在市东郊“集中劳动”(他没明说那就是劳改,我也就尊重他的意思,也写成“劳动”),时间恰巧与“自然灾害”时期重叠,累点还能扛,就是饿难以忍受。为了充饥,他们曾去农民收获过的番薯地里翻找细小的根须,洗洗后便生吞硬咽;三更半夜偷偷摸进厨房,从蒸笼布上刮下粘于其上的皮屑……
他还不无遗憾地说到,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读完大三、大四后,还得回过头来修大二未完成的学业,只为拿满学分。无奈家里已经没有能力供他继续读书,只得回武汉,最后还奉父命成婚,所以他只拿到了学业证,这对他晚年的职称评定造成很大影响,尽管他专业名声再大,最后却连个讲师、翻译职称都没有评上,工资便少得可怜,还好那些兼职收益给了他很大助力,否则他那一大家子捉襟见肘的艰难可以想象。
我总结似的感叹:“您要是当年安心把书读完,可能就没后来这么多事了,您亏大啦!”叔叔听罢,说:“你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不是不想读书啊,你想想,就是你的亲人被人无端欺负了,你都会上前拼命吧?何况是你的国家遭人欺?不能忍啊!” 叔叔说这话时,我的心弦像是被什么拨动了一下,但还没有情感波澜。他那时已经有点酒意,蜷缩在一张椅子里,语言平淡,像个与人唠嗑的邻家老头,让人无法把他与历史云烟中意气风发地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人交流的青年翻译联想起来。但叔叔的这番话我记下了。有一种记忆留在了心里,可能当时你会不以为意,但时间长了,就会发酵,会发光,会照亮你精神的城堡,乃至使你升华的灵魂想在天地间长啸!
叔叔真正进入我的心里,一定是从那时开始的!

魂牵彩云之南
前不久,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上的发言说到:“任何一段伟大的历史都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它值得后人以各种方式纪念和铭记。”叔叔啊,您在天堂听到这话,有何感慨呢?我的感慨是:这世上,最难磨灭的是公道!

本来,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我不喜欢写过长文章,以免读者产生阅读疲劳。但我这个人认死理。老实说,有个疑问一直缠绕于心: 叔叔回老家武汉并成婚了,那云南母女怎么办?难道叔叔会弃她们而不顾吗?这不像叔叔的为人啊。为这,我向张志鸿求证过,张志鸿回答,情况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通信是有的。但他说看过叔叔写的《钗头凤》,叔叔是很郑重地给他看的,他已记不很全,只记得其中有“娇身寒,夜阑珊”之句。
宋代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很早我就读过,这首词伴生的凄婉故事让人心碎。无法看到叔叔写的《钗头凤》,但叔叔把《钗头凤》中的陆游奉为知己,互为镜像,让我能推断出叔叔面对那次被家族安排的婚姻的抵制,已全无投笔从戎时的果决。是啊,“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且不说爷爷的家族是个封建意识很强的存在,叔叔那不被家族认可的婚姻只得无疾而终,更何况叔叔后来的破碎人生,坎坷境遇早已让他无法回头,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更是让他自顾不暇,精力疲惫,狼狈不堪。
但相信他从此便一直活在对云南母女的愧疚、自责与牵挂之中,一种无法对人言说的灵魂煎熬会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这又不同于岁月曾经赐与他的肉体折磨,而是一种良心的自我鞭笞,因此更让人同情与心碎!
他晚年越来越想去云南,见见云南母女,了却此生唯一的心愿,但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
十几年前,有一首歌广为传唱,名叫《彩云之南》,我在前不久无意中听到这首歌时,被它的歌词深深打动,我猛然觉得那首歌好像是为叔叔而作!叔叔,您那《钗头凤》我无缘读到,但相信这首歌能唱出您的心声。那句“往事芬芳”,多么贴切,它会让您想起您战乱中的爱情,还有您曾经的荣光!
叔叔,我把这首歌的歌词摘录了一些给您看,我会把歌曲放给您听,相信这当代人唱的歌,能让您沐浴属于您的霞光——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
彩云之南归去的地方。
记得那时那里的天多湛蓝,
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
这世界变幻无常如今你又在何方?
原谅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
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
不虚此行别遗憾,
往事芬芳,
随风飘扬。
叔叔,您听到了吗?歌声中,我仿佛看到,您在用思念当墨,写着属于您的《钗头凤》,泪流满面;那位救过您的姑娘,彩云之下,正踮起牵挂的脚尖,眺望远天嘶哑的鸣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