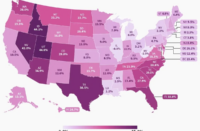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在国际访问学者邀请函上特别说明:“您可以全方位地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对于这条表述,起初我很不以为然,心想:这还有必要特别说一句?其实心里揣着的是对“图书馆”遥远模糊的记忆和如今满满的陌生感。在手机就是随身百科全书的时代,无论是母校清华大学当年那几座藏书建筑,还是海淀白石桥边上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三环十里河边上的首都图书馆,上次去是啥时候,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黄熹珠馆长
抵美后的第二次例行会议,UNC 东亚图书馆馆长黄熹珠就带着她的韩国助手来到传媒学院的课堂上。两位配合为我们以中、韩学者为主的团队介绍大学图书馆的使用方法。我们感叹现代大学图书馆网络检索系统的强大,也钦佩她们主动上门服务的精神。作为东亚图书馆的馆长,黄熹珠女士与人交流的方式亲切得体、平易近人,身上那股子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乐于助人的情绪足以感染在场的每个人。在大课堂英文介绍结束以后,她又主动走近中国学者,用中文征询我们有没有任何关于图书馆、关于学习的问题,并表示如果需要帮助,她一定尽力。
这项对三角地华裔教授的访谈项目,最初就是这样开始付诸实施的。凭借黄熹珠馆长精心筛选后提供的一份 UNC 教授名单,我才敲开了第一位受访对象: UNC 亚洲研究系萧丽玲教授的大门。
服务,图书馆的第一要旨
航(刘航):感谢黄熹珠馆长对我们访谈项目的大力支持!
黄(黄熹珠馆长,以下简称“黄”):不用客气,能够帮助到你,更何况还有可能通过你来帮助到未来的留学生,我很高兴。
航:在您帮我提供访谈线索以后,我又陆续听到很多身边小伙伴儿对图书馆工作的赞叹。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学者,要写关于茅盾先生的论文,想找到茅盾当年在海外出版的一本非常偏门的书,她说起初在咱们这儿没找到,后来你们居然在芝加哥大学帮她调到了这本书!
黄:馆际互借制度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之一,服务的人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一下子想不起来。
航:那是不是说我如果想要找一本书,只要提供书名,你们就可能调动全美的图书馆资源帮我找到呢?
黄:是的。只要是师生教学、科研所需的资料,我们都会尽可能地帮忙寻找。即使有时候正常的馆际互借行不通,我们也会尽自己的努力,通过其他途径去找书。这样的例子很多,甚至不局限在美国或在本校。比如我有一次去南部的埃默里大学开会,认识了他们图书馆的一位同行,他提起说他们一个老师,需要一篇中国台湾日据时代的博士论文,现在那篇论文收藏在台湾大学,但因为版权的关系,台湾方面不允许馆际互借,这个馆员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就希望我来帮忙。
于是我就帮助他写了 E-mail给台大,详细询问了他们为什么日据时代的资料到现在仍然有版权的保护。对方说的确有规定不允许外借,说“你们如果特别需要,可以到馆来使用”。
可是,我们毕竟在国外,真让这位教授为了一篇论文跑去台湾一趟也是不大现实。我就想,如果整本的博士论文没有办法外借,那么我们就分章节来借阅可不可以?因为我了解,版权法里有一个条文,叫作“合理使用”。在此条文下, 使用 20% 以内的内容可以不用授权。所以说一本书可以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试用、试读”。
航:这真是得有“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办”的精神,才能这么上心地想办法。看来这种服务精神和馆际互借的流通方式是全美的大学图书馆都推崇的。
黄:全美的大学图书馆对资源共享和相关的服务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东亚图书馆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东亚图书馆的服务相对更专业。有难题时,我们自己馆内如果没有其他专业的馆员能帮上忙,协会同行就成了我们求教的对象。同行们虽各在不同学校工作,但大家一回生二回熟,在专业上会经常互相帮忙。最后,通过我们的努力,台大图书馆正在欧洲开会的馆长远程交代:认可我们的方案。我们就这样一章一章地借出来给那位老师使用,最后达到了学术服务的目的。我还挺高兴埃默里大学的馆员主动联系我,让我也多个机会增长经验,能把这件事做成功,自己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航:您这里除了能帮老师、学生、学者,找书、找论文、找名单以外,还管找什么?
黄:哈哈,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觉得学生做的项目有实际的需要,甚至会帮助他们找钱。
最近就有个例子,我们有个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需要的资料很偏,他跟他的导师要找到一些中国 1951年至 1963年间华中地区的报纸,来研究当时家庭生活方面的内容。
航:我是报社出来的,几张老报纸真有这么难找吗?
黄:在海外,要找国内早期的报纸,算是相当困难。于是我就去找我在国内有过良好合作的代理供应商。我们在工作上和行业专业会议上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我和这些厂商的关系,说是买卖,不如说是行业上的合作伙伴,彼此都很尊重。我这么多年很努力地维系这些关系,这一次他们还真的是帮上了忙。北京的一个代理商通过努力,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些报纸的缩微品。要知道报纸原版很难保存,在有数字化之前,保存报纸这类纸张脆弱的出版物,最好的就是把原版转制成缩微品。缩微品制作成本很高,加上一般只有图书馆之类的有典藏责任和需求的机构才会留存,所以价格一般是很昂贵的。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美元。这么多钱让学生自己承担根本不可能,即使用我们年度计划里一般买书的钱,负担如此昂贵的出版品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于是跟学生说,钱就让我来想办法吧!其实,当时我心里也还没有把握呢。
航:要多少钱?
黄:五份当年华中地区的报纸微缩品(期数还不全),使用 DVD刻录过来,加上手续费要 8000~10000美元。但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其他渠道都找不到那个年代的东西。视野范围内看到的,从那时保留下来的,只有在国家图书馆的这么多。
航:天呐,我来美国之前把我自己这些年留存的有自己文章和照片的报纸,十几年几百份都拍了数码照片,原版统统卖了废纸。听您这么一说我这是扔掉了多么大一笔钱。
黄:对我们图书馆专业来说,报纸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被不同人看到有可能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或研究观点。还有一些学者就是因为现有馆藏中有这个原始资料,才延伸出了某一项研究。前几年我就刚好收到一大批民国时期的妇女杂志,那么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历史系教授,看到我们有这个东西,非常兴奋,就毫不犹豫地开展了一项新的研究项目。馆藏建设这项工作,有时候还很难讲,究竟是研究者带领我们丰富馆藏,还是我们的馆藏引领了研究者的科研学术项目。
航:需要 8000多美元购买几份缩印版转制的 DVD。那么您后来究竟是如何帮这个学生找到钱的?
黄:我答应了学生以后,转回头就去找我图书馆的同人问:“我记得我们图书馆每年有好几个不同专项的资金,其中有一项捐赠专款,是用来支持研究生去买昂贵的研究资源,是吗?”那位同人肯定了我的询问,我接着又问这个款项一般资助的标准如何?他说,一般是每位研究者 500美元。我说:“500美元呀,太少了,我现在有一个学生有这样的情况至少要 8000美元。”我直率地问:“这笔钱你统统给资助了行不行?”
航:您这款募的……
黄:哈,可不是嘛,通过我一再游说,还真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我在我们图书馆有一个绰号,叫 Trouble(麻烦),职责所在,我这个人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像这个学生,如果我没有帮他找到这些资料,那么他就没有继续进行这个项目的可能,就得改研究题目,我们做服务,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发生。除非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只要能想到办法,I will do it! 说实话,我的同事给我这个绰号,算是对我工作上的肯定。我还挺高兴被叫Trouble 呢!
航:在我们的印象里,传统的图书馆首先强调的大部分都是馆藏的多少,那么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不比馆藏,开始比服务质量了?
黄: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就整体开始转变办馆思维,开始借用工商管理、客户服务关系的理念来办馆了。
航:“客户是上帝”,被你们用在这儿了。
黄:这一时期,美国的科技飞速发展,对各行各业固有的经营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读者对信息和图书馆的使用行为也跟着在改变,我们意识到丰富馆藏已经不能是图书馆追求的唯一目的。之前一提起某个图书馆,就经常要问藏书量。要知道,在纸书时代,馆藏数量的多少,往往是跟办馆历史有关系的。新想法是:如果我们每个用户的所需都能满足,那馆藏多少有关系吗?馆藏是静态的, 如果藏书都不能被使用,那么再多的馆藏又能如何呢? 在新经营理念下,像我们 UNC的东亚图书馆,成立时间比起美国大学最早的一批东亚图书馆晚了七八十年,但我们能及时以服务和接轨新科技来实现和读者间的互动。
航:追求馆藏量的理念看来是过时了。
黄:馆藏建设的工作仍然还是很重要的。只是在数字时代,它已不是图书馆唯一的重点工作。图书馆肩负着保存人类知识和文化记录的责任这是不会变的。美国大学里的东亚图书馆,在芝加哥大学老馆长钱存训先生那个时代,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战乱中把国内珍贵的善本带到美国保存,在新时代国内逐渐改革开放以后,又把完整的影印版交回给北京以及国内的其他图书馆,得以向公众开放。他有他的眼光和胸襟,完成了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
即使在当今时代,我们还会以钱教授他们那一代图书馆人为榜样,去尽量保存历史。但要服务新一代的图书馆用户,这就远远不够。更何况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都已经严重缺乏书籍上架空间。这几年来,全国大型的图书馆都纷纷在兴建
校外的图书仓库。2008年以后,美国受经济萧条的冲击,充实馆藏的经费没有以前那么充足了,我们不能再按往常那样有多少钱就毫无顾忌地去买书。再说,书买回来以后,还得编目处理,这些费用也是挺昂贵的。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理念也就因此种种因素开始改变。
现在我们提出了“ResearchServiceCycle”(服务生命周期)的理念。以前就是书在这里,你拿吧!现在变成我们主动出击,全身心地服务学生、老师,还有社区居民、社会大众。

UNC图书馆公共空间,学生们在图书馆可以完全以最放松的状态进行学习,甚至躺下休息、小憩等
航:社区居民和社会大众也可以来大学图书馆借书、看书吗?
黄:UNC是公立大学,图书馆对社区群众完全开门,不但他们可以来图书馆读书,居民只要自己办一张卡(10美元)就可以借书和使用电子资源,他们还可以和馆员联系,要求做咨商。
海外读书,要有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心态
航:我之前去 NCSU(北卡州立大学)采访,发现他们图书馆可能是更新一些的缘故,服务的科技含量比我们这边还要高,甚至是机器人在帮学生取书。现代大学图书馆除了服务思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硬件上、网络数字化管理方面也肯定是过去不可比拟的。
黄:这是潮流和趋势。硬件大家都在不断地更新,数字化本身更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新一代的读者,由于网络方便,也不见得需要到图书馆里来才能拿到资讯。这种资讯获取行为,导致有些年轻学生甚至认为他们在 Internet(浏览器) 上 Google不到的东西,就代表那个概念或东西没有存在过。因此,图书馆不能懈怠,必须把资源服务的转型工作做好,以配合现代人图书资源使用的新行为和研究需求。
但你知道,往往是越大、历史越悠久的图书馆,接轨新科技的难度也越大。新出版物直接做电子版相对容易,旧的文化、学术、知识,载体都是纸质书,编目和数字化的工程相当耗时费力。UNC图书馆这几十年来做得还不错,20世纪90年代时由 Google公司出技术所发起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基本完成了英文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这个投资成本很高,但对汉语图书数字化的进度相对要慢一些,因为汉字是方块字,数字代码跟英文不一样,技术操作难度较高。还有汉字数字化开展计划之前,还得先解决许多语言学上的难题,比如字根解析和如何整合汉字,更何况在东亚国家通用的“字”,很多“形同意不同”,还有一些意思相近的字,写法、读音又不相同。
航:数字化以后,您认为我们使用图书馆,更应该注重它哪方面的功能?或者说在数字和网络的时代,我们该怎样去使用图书馆?
黄:我觉得技术的进步是形式上的,学习的关键还要看人本身有没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去获取新的知识,去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
航:有点儿宏观,您给解释解释。
黄:新技术让我们很容易接触大量的资讯。话题上有我们熟悉的、认同的, 也有理念上新异的、我们不习惯的,内容有经过严谨制作的,也有粗糙组合成的,等等。面对杂陈的资讯,我们个人的心态是开放兼容的,还是僵化守旧的? 这会直接影响我们获取新知识的效果和适应不断变化世界的能力。我给学生上图书馆课时一定加上一个结语:面对得来容易的大量资讯,能否有效利用资讯来学习,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从,而是取决于自己是否有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 去辨别和选择信息。作者、出版者是谁?他们的背景如何?这本书究竟属于哪一种出版性质?出版内容的质量如何?是建立在严谨的研究基础上吗?数据来源究竟是哪里?在数字化时代,不具备思辨的能力,那么被误导相对也更容易。

UNC 图书馆廊道
另外,我也想分享一下,从馆藏建设的角度对馆藏使用的一些想法,这和数字化无关。我们东亚馆除了收集中国大陆的学术出版书籍,还收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以中文在其他国家出版的书。由于我们需要满足学校教学和研究所需,我们的馆藏除了有一般的学术出版,也会收集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本地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的文本。在馆藏工作中,历史事件就是一桩历史事件,和它有关的文献就是文献,在我们眼中它们没有美丑之分。对历史做评判不是馆员的职责,那是学者、研究者的任务。馆藏是要能及时保留下这些人类历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记录。我有机会和读者接触时,会鼓励他们放宽心境和眼界来浏览和使用我们的馆藏,我也很欢迎读者给我们的馆藏建设提建议。这么多年在这个工作上磨炼,也使我受益不少。我做文献收集工作时间久了,也练就了一双能够超越自我意识的眼睛。
航:练就了一双穿透历史的眼睛。
黄:人们每一天都在创造这个时代的历史。书或电子出版物其实是对日常生活一种有取舍的记录,取舍的角度各有不同,单一角度的陈述并不代表就是对事物全貌的认知。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向来主张针对一个事件,越多角度地解读, 越可能使读者接近事物本来的面貌。所以,我会让我的馆藏尽可能地提供给读者多角度的资料。针对一个作者的观点,“你可以不赞成,但我不能没有!” 没有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判断,就可能带来人认识上的偏差。
航:所以你们会尽可能针对一个事件,收录不同角度的人出版的不同的三本书吗?
黄:Yes!只要是严谨,优质的学术出版和文献,我们尽量做到。
航: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可能会不断挑战自己以往的认知?
黄: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台湾已经逐渐开放了。但说实话,对我来说冲击还是蛮大的。我的基础教育,小学、初中,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台湾。1984年来到这边,一下子看到有关台湾的很多完全不同的书, 里面的观点都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我常常感到很困惑。
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在美国出版的书,书名我已经不记得了,是关于蒋介石本人生活的,是他身边随从的记录。书中记载和描述的蒋介石跟我在台湾所被教育到和读到的很不一样。在这本书中,从各个事件的描述里,蒋介石呈现的就是个脾气暴躁、个性浮躁的人,远不是我们此前知道的慈祥、伟大、英明的领导。我这才意识到,之前我接触到的历史是经过过滤的,领导人都被神圣化了。这件事情对我本身的冲击力很大。
今天在如此多元化的世界,我们的学生接受这类冲击的机会会更多。美国这边的电视上天天在说“朝核”问题,在说“中国威胁论”。那么来到我们东亚图书馆,你去找一找有关那个地区的历史书籍,阅读分析后你自己便可以得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而不是跟在新闻评论员的观点背后走。
还是那句话,心态决定一切。面对一件事,多看几个角度……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航:我在咱们的电子阅览室还看到有很多视频资料。有些影片我在互联网上都没有找到,居然在我们图书馆的视频阅览室里很轻松地观看到。
黄:我们购买了很多来自各个渠道的纪录片,不被各种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电影等都有,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阅览室看,或者借回家看,都是可以的。
从事图书馆专业需要的准备
航:作为前辈,您给介绍介绍,未来如果要去学习图书馆管理专业,现在要做哪些准备?怎么知道我合不合适,喜不喜欢做图书馆专业?
黄:说老实话,科技发展太快!以后图书馆会变成怎么样,我都不敢讲。有两点我想是重要的基础:第一,自我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的培养和对信息技术的跟进;第二,扩大自己的视野、知识面,提高学习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个人基本素质的强化,比只专注特定技术能力的准备,我看会更有持久性。因为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今天学的明天可能就过时了。你已经看到我们附近的大学图书馆开始用机器人在取书,那么人工重复性的工作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被替代。但个人的文化和知识素养、历史观、世界观的养成是个积累的过程,眼下看,机器人还很难取代,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人的核心价值。技术的更新最多是硬件上的转换,没有信息内容技术只是个空壳。
所以,从自己喜好,有兴趣的东西开始,一步步锻炼跟进,在图书信息这个专业都可以有机会发挥。我今天的工作和我在研究所所学的也不一样,当年我进入图书馆行业,是从编目馆员做起。编目的工作讲求的是细心,有能力解读枯燥的编目条文和按标准规范实行编目。以我年轻时候的个性,这个工作对我可能就不太合适。可是,几年下来,编目这个工作帮我练就了扎实的做书目和数据处理的基本功夫。这些“功夫”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图书馆快速转型时,不但对我在工作上的适应帮助很大,而且让我更能在现在的工作中,针对电子出版物中文数据处理的问题,有效地和出版商以及系统技术人员进行沟通。
说了一堆,最后我只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来到美国,要能够“Openyoureyes”“Openyourmind”!不断尝试一些新东西,不要让自己原有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始终约束着自己,这样才能学得更多,收获更大。
航:好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并为我们的项目提供帮助!
黄:不客气,也希望我说的能够对读者有一些帮助。